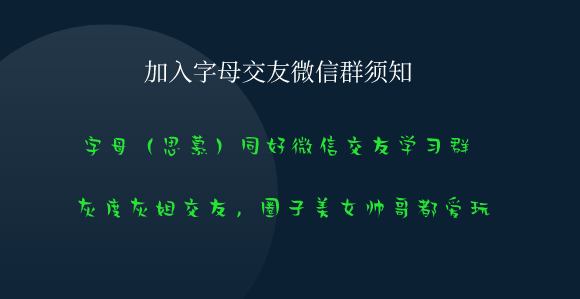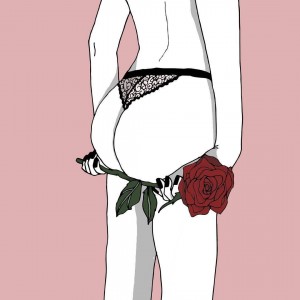当我和一个娇滴滴的野男人在酒店邂逅,紧要关头,这家伙竟然翘起了兰花指,取出小雨伞,接着花了一整首歌的功夫,用湿巾仔细擦拭干净上面的油迹。
我撑起胳膊,侧躺在被子上,从失败者的视角仰视他,你特吗在干嘛?
他笑着回答我,怎么能那么草率呢,我们需要一点点仪式感。
我忽然发觉,作为一个女人,自己活的未免有点太糙了。真的,在这之前,我只不过随便冲了个澡,对面呢,已经给自己洗刷了不下三遍,并且抹上了好几层身体乳了。
我怎么也没想明白,究竟是怎样的狗血生活,催生了如此高傲的尤物。
小兔最近一直闷闷不乐,大晚上的不睡觉,跑来我家的沙发上,折腾我刚收到的水仙。
我有个坏习惯,只要是收到的花儿,一定会在家里找个花瓶,插进去摆好,当然,花瓶里是有水的,偶尔还会加几滴营养液。这种神秘液体来自某宝,几块钱一瓶,便宜的很,但能直接决定花儿的死活。
滑稽的是,有些野男人在我这的生命力,甚至还不如几朵花顽强。通常到了男人先一步枯萎的时候,我就会果断把花整束拔出,通通扔进楼下的垃圾桶。
不需要很久,花瓶里一定会有新的生命出现。新花儿代表的,并不是性瘾患者朝三暮四,而是我作为大龄单身女人最后的尊严。
我一度相信,不开心是有传染性的,就行女人来姨妈,都是会传染的。
大学宿舍里的几个女生,从开学的陌生,慢慢到无所不谈,忽然的某一天,老大说,老伙计们,我来姨妈了。接着在短短的一两天内,老二老三老四惊恐的发现,自己的亲戚竟然也跟着来了。
一般情况下,女生宿舍会把这一天的到来,称为舍友情谊的“独立日”。
小圈子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,悄无声息,潜移默化,到了有所察觉的时刻,早已无力回天,连身体的自然反应都逃不过。
我说小兔,刁姐是被折腾怕了才不开心,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啊。
小兔玩腻了百合花瓣,揪了撮刘海在手里打卷儿,差不多要把那撮毛拔光,有气无力的回应我,晨儿,我只是有点想老王了。
我掏出手机,贴在小兔的脸上,圈儿里这么多小鲜肉帅大叔,真的不考虑一下?
小兔重重的把自己摔进沙发里,活脱脱一只被拆了线的木偶,话都懒得说。
我大概能理解这种无奈,如果把男人比喻成女人的食物,那有些男人就是主食,有些男人则是调料,还有些男人呢,是精神食粮。可偏偏这个来自成都的小女人,无辣不欢。
王老师这颗小米椒,已经被家庭牢牢的拴住了。小兔除了闷闷不乐别无选择,我也不会允许她做其他选择。我比小兔大的这几岁,可不只体现在眼角的皱纹上。
和有家室的男人接触,最忌讳的,就是把自己陷进去。
天天吃调料,会把身体吃坏的。
和这个娇滴滴的男人见面,我不得不强行给自己找个借口。我真的,只是为了给苍白无聊的日子,加点调料。
上我曾经认为,女人只要精神富足,就能把生活过的有姿有色。可实际上呢,直到我发现,自己并不是被闺蜜的不开心传染,真正苦闷的源头,还是出在男人身。
我这段时间所面对的男人,确实太单调了。老海,这个只愿意陪我一人的老男人,和我一起走过很多黑暗的路,可恰恰我最需要的东西,他不能给。那个东西的名字,叫自由。随便在圈儿里找个男人邂逅,就是我最简单的自由。
酒店应该一早就猜到,来住宿的人,真正想看电视的并不多。
陌生男女相见,惯例插卡取电锁门,最多再加个开空调的步骤。倘若寒暄后依然冷场,为了掩饰过于尴尬的氛围,打开电视确实是最好的选择。我们这一代,已经很少有人正经到还愿意认真看电视了。
不是说我们这群人不正经,而是电视这个传统媒介,太过正经。
娇滴滴在卫生间洗澡的空档,我差不多把电视机节目从前到后翻了个遍,最终确认了一个事实,姐真的是个不正经的女人。
我只好踮脚从桌上拿了包,把指甲刀翻了出来,慢慢消磨时间。
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,解决用户投诉电梯过慢最有效的途径,就是在电梯里装几块玻璃。因为人只要开始关注自己,就会忘记外界的变化。论消磨时光,剪指甲和照镜子一样实用。
不过和娇滴滴不同,像我这种不注重仪式感的女人,剪脚指甲和手指甲,用的都是同一把刀。我唯一坚持的底线,这把指甲刀,只能我一个人用。曾经有无数个男人,在床上打过这把指甲刀的主意,通通被我严词拒绝。我和他们说,你想剪手也就罢了,还想要剪脚,是想把脚气传染给我吗?
男人们一般在这个时候,都会非常严肃的证明自己没有脚气,努力做出夸张的姿势,把脚扭到鼻子前,深深吸一口。
最后还要告诉我,你看,我的脚不臭啊,不信你闻闻。
无一例外,我会直接走人。
我承认,当娇滴滴裹了浴巾头戴浴帽,以十分妖娆的姿态推开门,作为一个女人,我败了,而且败的不止一点半点。
这种心悦诚服的溃败,很难用表情掩饰,我只好打了个哈哈,一边说话一边找机会把指甲刀藏起来。
等待P友洗澡的时间剪脚趾甲,说到底还是不太体面。
我说,小哥哥,你可真白啊,平时很注重保养吧?
娇滴滴竟然抱住胸口做害羞状,哎呀哎呀,哪里哪里,你也很白啦,要不等下你试试我这个牌子的身体乳,我拖朋友从国外带来的,不骗你,可好用了。
我强忍住胃里的翻涌,算了,来都来了。前两天我还用这四个字,在医院劝说刁姐留下,果真报应不爽,好人从来都是没有好下场的。
来都来了。
努力调整情绪,我闭上眼睛,想象房间里的男人是彭于晏,只是等了半天,一点动静都没有。
睁开眼看,这家伙竟然翘起了兰花指,取出小雨伞,用湿巾仔细擦拭上面的油迹。
我撑起胳膊,侧躺在被子上,从失败者的视角仰视他,大哥,你特吗在干嘛?
他笑着回答我,怎么能那么草率呢,我们需要一点点仪式感。
我忽然想起圈里的一位前辈说过的话,他说,如果有人让你吃屎,你一定要从开始就学会拒绝,不然吃着吃着,就会慢慢习惯屎的口感,真的开始吃屎了。
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,和吃屎没什么分别。
我直接起身,掏出藏在枕头下的指甲刀,先修了一下手指甲,又慢慢开始修脚。
娇滴滴停下了手头擦拭的动作,差点把湿巾丢了,一脸震惊,你,你在做什么?
我说,你看不到吗,我在修脚呀。
以我的柔韧度,脚放在脖子后面都绰绰有余。
我轻松把脚抬起,放到鼻子面前,深深吸了一口气,装出陶醉的表情。
接着我把脚直接伸过去,几乎要撞到娇滴滴的鼻子,娇滴滴飞身下床躲开,转头立马开始穿衣服。
我说,你别走啊,我的脚不臭的,
不信你闻闻,真的不臭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