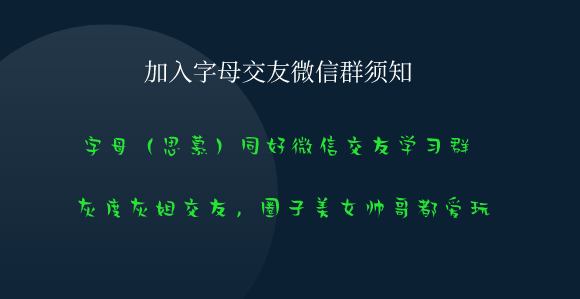z先生问我飞机几点到,来接我。但我拒绝了,我选择独自前往市中心。他表示无语但不置可否,我没说话,我是为了我自己。

第二天在z先生的车上我终于见到了他,灰色的衬衫袖口挽起露出小臂,握着方向盘的手指还算好看,但我有一丝不爽,这个人太淡定了,就好像和我见面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一样。于是我努力捕捉他的所有细节,从偶尔瞟过来眼光中,终于发现他的眼睛还是亮的。
车里放着一首不算吵闹的后摇,他跟着节奏轻声哼唱,这个男人心情不错。在递给我水的时候我们手指无意间触碰,只是一刹,感觉手指擦过有了轻微的触电感,我想我可能脸红了。可我早已经不是那个满心浪漫的小女孩,会因为这样的细节心跳不止,扭头看向窗外,广州的夜灯如流火。
z先生用单手开着车,忽然刹车从后座拿过他的西装外套扔到我的腿上,
我穿的是及膝的裙子,他说广州的冬天不冷,但也够呛,盖着。
我忍住笑只是勾勒一下嘴角,自从结束了感情开始游走在不同人之间,我早已不是那个会被细节温柔到的人,在男女接触中,不过是互为猎人和猎手,一切言行都是有目的性的算计。但是我还是因为这一举动看了他一眼,窗外夜色如水,他的轮廓很清晰,我多看了两秒。
仅仅是两秒而已,这个该死的男人捕捉到了这个细节,然后很自然的伸手把我挽进怀里,凑在我耳边微声说:终于来了啊。
不知为什么,我忽然用力抱紧了这个男人,该死的男人。
吃完饭后他牵着我的手进入了酒店,打开门是他特意选的带地毯的房间,这时候我终于发现我不具备作为猎人的素养,他好像都算好了。正当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,他从身后靠过来,说:g下吧。
我还在想该怎么办的时候,膝盖已经触到结实的地毯了,不算厚,触感也不软,不那么舒服。z先生摆弄着工具,然后拿着一根黑色的缎子向我走来,遮住我的眼睛然后打结,我的目光所及立刻一片黑暗。
很多细节我并不想描述,那一次的过程其实是十分波折的,我以为我游走在不同的人之间,技艺娴熟,拿下这样一个老东西自然不在话下,但我失算了。他平静的看着我的卖力,如同在看马戏团的表演一般,然后他示意我停止,摁住我,拎起一根有波纹光泽的戒尺,痛感从背后传来,我忍不住叫出声,又十分xx耻的想到这叫声怎么特么的跟发春的猫一样。
不知道戒尺什么时候停下来的,只知道我瘫g在地毯上抱着他的腿,背后的痛感是灼热的,脸上的眼泪是凉的,他的手覆盖在我的头顶是暖的,片刻后他拿纸巾给我擦脸,顺带擦掉我不知什么时候和眼泪一起飙出的鼻涕。我问他:不嫌弃吗?
z先生说:
「你tm拿我当什么人」
他说:
「对自己负责,或是不负责,这一刻我在这里,我带领你」
他还说:
「不要紧,我来了」